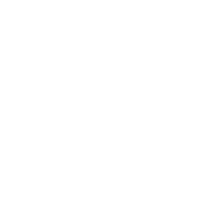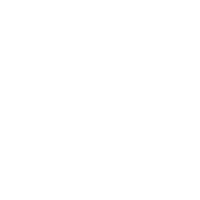挺笔荷枪 清风傲骨

邓拓
家住福州,每次来到乌山,穿行在一片修长茂盛的翠竹间,我都会向乌山北麓天皇岭东北坡的“第一山房”投去崇仰的目光。这个第一山房,据说得名来自房后为米芾手迹的“第一山”题刻。院门白墙上,嵌着一块开国上将肖克将军题写的“邓拓故居”牌匾,这就是新闻界泰斗、史学家、杂文家、诗人,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邓拓的出生地。
邓拓故居的门牌号是“第一山7号”。走进门头房,迎面是一座绿意葱茏的小山,曲径环绕,巨石当空,竹影婆娑,芭蕉摇曳,虽小而仄,却巧且雅,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故居倚山而建,推窗望去,山、房、石、树容于一隅,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奇妙构思。山前的摩崖石刻上,镌刻着邓拓的一首诗:“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志情。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那是邓拓1963年写给北京市委杨述的一首诗,诗中充溢着邓拓对革命事业不懈的追求。
主楼是一座三间排双层木构小楼房,坐北朝南,悬山顶,为清末民初福州旧民居风格建筑。1912年2月26日,邓拓出生在左厢房,父亲给他取了个乳名叫“旭初”。主楼西侧有一间书房,即邓拓卧室。现辟作展室,陈列“邓拓生平展”,按他跌宕光辉的一生脉络分为“邓拓生平”“邓拓著作”“怀念邓拓”三部分,丝丝缕缕体现着邓拓刚直清正、无私无畏、博学传奇的一生。
对于我这个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与邓拓的“相遇”,是通过阅读他诸多著作得以实现的。我也算他的小“同乡”,因崇仰名人、学文习作的缘故,常徜徉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篇篇精彩诗文中,或击掌,或叹息,或吟咏,或共鸣,许多的日月光华都谨记着他所言的要珍惜“生命的三分之一”。每当抚摩着典雅的《邓拓诗集》,以及流传至今仍为读者喜爱、老舍赞“用大手笔写小文章”的《燕山夜话》,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燕山夜话》,邓拓仿佛信手拈来,天文地理、史实掌故、农桑医术、哲学历史、书画读书、风情习俗等,旁征博引,娓娓谈吐,或针砭时弊,或解答生活疑难,将思想与知识熔为一炉,让人仿佛沐浴在历史、实践与科学的海洋。
1919年的夏天,邓拓入“闽侯小学”读书,学名邓子健。四年后升入福州三牧坊中学(现为福建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年仅16岁的邓拓就与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的傅衣凌等同学共同创立了“野草社”,并自费出版了他们自己编著的刊物《野草》。1929年,邓拓高中毕业,考入光华大学。
在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邓拓离开家,从闽江口乘船赴上海。夕阳晚照,他触景生情,写下《别家》:“空林方落照,残色染寒枝。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家山何郁郁,白日亦凄凄。忽动壮游志,昂首天柱低。”这首诗记录了他对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次年,18岁的邓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冬,在纪念广州起义的一次活动中,邓拓被捕送往南京,后押至苏州军人反省院。当时,三哥邓叔群已是著名的科学家,经他多方奔走,后由蔡元培、褚民谊等人保释,邓拓终于于1933年秋出狱回闽。同一年,应同学李拓之之邀,邓拓避居上海,又一次离开故乡。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少年执笔复从戎,不为虚名不为功,独念万众梯航苦,欲看坦荡九州同”的邓拓,给双亲写下这首诗后,就直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始他一生为之奋斗且激情四溢的“战史编成三千页”的新闻报业生涯。
边区10年,邓拓带领《晋察冀日报》的同志们跋山涉水,在敌人的一次次清剿围合、扫荡袭扰中坚持出报,及时把前线的消息传向四方,鼓舞士气,成为边区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喉舌。在一次反扫荡转移中,他的马中弹,自己则死里逃生。“挺笔荷枪笑去来,巍巍恒岳岂能摧。”这是邓拓在那个艰苦的年月里写下的诗句。《晋察冀日报》从创办到终刊,共出版了2800多期,低劣的物质条件与生活上的困难,以及交通的不便,使印刷报纸所需的油墨、纸张甚至铅字等,都难以为继,邓拓发动大家自力更生,用铅坯翻铸成字模,再铸成铅字,报纸用的油墨,也是用老乡家里锅底的烟灰制成的……当时报社内流传着“八头骡子办报”和“三千字内做文章”的佳话。他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主编出版了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
新中国成立后,邓拓受命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兼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中央指导下,邓拓主持《人民日报》改版,他身先士卒,亲临一线,不仅为报纸写了大量的社论,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积极书写现实生活的署名文章。
1958年8月,邓拓被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离开了战斗近10年的岗位。1959年2月12日下午,邓拓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参加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他百感交集,写下了“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的诗句。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邓拓又把思考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并以直达人心的笔触给人们留下了以马南邨为笔名的《燕山夜话》,以及和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闪耀着哲理和诗情的杂文随笔。
但之后,当“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而来时,邓拓和他的作品一起遭受不幸,令人扼腕叹息……
2014年4月的清明时节,我又走进这座山房。沿着木质的楼梯走上二楼,转角处仿佛听见了时光的一声叹息,而留在古都榕城的这座小楼,依旧是儒雅的笑容。门廊的两扇木门虚掩着,扇形的拱窗正似邓拓先生一直喜欢的折扇题画的样子,迎面正对山坡的迎春花,垂着漫涌的翠绿枝丫,一盏红灯笼轻盈地挂在门廊处。倚着小楼,我望见了在春天里盛开的山茶花、三角梅、蔷薇花、紫藤花……似乎看见邓拓在远离故土的京城写下他对山茶花、梅花高洁秉性的喜爱,听见了他儿时的琅琅读书声。透过高高的苹婆树,乌塔的葫芦顶塔刹仿佛又传来他的诗句:“风送塔铃遥自语,月沉鸟静梦初圆。”
时空交错的印痕,鲜明且战栗地再一次击中我的心怀。转身处,又见一楼右侧厅中立着邓拓在北京家中书屋的立体像,以及他身着中山装凝思的影像。远远地望去,先生清风傲骨,遥看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