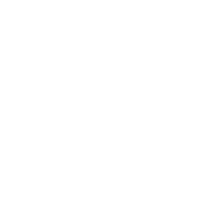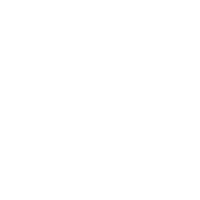为古籍传播链寻找失落的环节
——写在《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出版之际
方彦寿

福建建阳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刻书中心。这种“著名”,以往主要是通过古今藏书目录和珍藏在国内外图书馆中众多的建本古籍体现出来,而对创造这些刻本的人,即所谓刻书家,却很少论及,以至难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晚清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在其学术名著《书林清话》中曾满怀期待地说:“(明代)刻书独多,为刘洪慎独斋、刘宗器安正堂,而皆建阳产。自宋至明六百年间,建阳书林擅天下之富,使有史家好事,当援《货殖传》之例增‘书林传’矣。”笔者早年读到这段话时,曾怦然心动,乃至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一“好事”者。于是,在撰写《建阳刻书史》的过程中,试着对其中关涉的刻书家史料加以特别留心和关注,并积少成多,陆续发表了若干篇以“刻书家”冠题的文章。其中,最早的是刊发在《文献》杂志1987年第1期的《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考述》,此为阐述单个刻书家的论文。其后,又有以“闽北若干位刻书家生平考略”,阐述刻书家群体的几篇文章,在《文献》《中国出版史研究》等期刊上陆续发表。再往后,我沉下心来,不急于撰文发稿,而是把目光从建阳、从闽北扩展至八闽,开始更加广泛地搜集资料。“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日积月累,眨眼之间30多年过去了,这部被我私下里称为“书林传”的《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终于问世了。
一、《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之概况
其实,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谓“书林传”,只是引发本书写作的一个诱因。主因则在于传统的古籍整理中,当涉及“人物”,其立足点往往是“整理者、编纂家和藏书家等”,而罕有所谓“刻书家”。于是,在历史文献从作者、编者、刊行和收藏这一传播链中,往往缺失了刊行这一环节。而这一环节的主要人物,就是刻书家。以这一观点对此前的相关成果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研究和介绍整理者、编纂家和藏书家的相关成果可以说相当丰富,而以刻书家为主题的成果,则十分有限,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此书的写作,能为古籍文献的传播链找回一个失落的环节。
全书主要以人物为中心,搜集整理了由宋至清福州、建宁府、泉州、兴化(今莆田)、南剑州(今南平)、邵武、漳州、汀州(今龙岩长汀)、福宁(今宁德)九地,以地域为单元,每地一卷,共分九卷。全书共收录812位官、私、坊刻书家的刻书事迹。在此九地中,刻书家最多、排名前三的建宁、福州和泉州三府州,是福建历史上刻书业最发达的地区。而建宁府又因刻书中心建阳为其属邑之故,以226位刻书家位居全闽之首。
在建宁府226位刻书家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外地的人士。如官员有宋代的韩元吉、蔡幼学、王埜、刘震孙和吴坚,明代的邵豳、张文麟、许应元、李东光、樊献科、邵廉、沈儆炌、魏时应和龚道立;学者有祝穆、杜本、张光祖、潘耒;宗教界人士有王日休、释慧空等。他们之所以来到建宁,主要就是受刻书中心建阳的吸引,要借助书坊的刻书技艺来出版他们撰写或编辑的著作。
所谓“以人物为中心”,指的是以图书刊刻者为基本线索,对其刊印之书和生平事迹尽力加以辨析和考述。以往的研究,或以时代为发展线索,或以历史事件、图书版本为依据,而罕有以刻书家为中心的。究其原因,盖因刻书业在历史上被视为一种商业行为,刻书家往往被蔑称为“书贾”,从事这一行业者社会地位不高,从而使从业者生平罕为记载而难以成文,更遑论成书了。
书名中的所谓“考略”,指书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刻书家的生平事迹,及对其所刊行的具体刻本的考证、辨析这两个方面。由于刻书家生平史料欠缺,或搜寻不易,使古籍刻本的鉴定容易产生一些错误,这在以往的古籍鉴定中屡见不鲜。在行文中,笔者努力把古籍刻本刊刻地点、刊刻年代的判别与刻书家的生平结合起来,力图以此纠正以往的一些误判。
二、《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之学术追求
1. 提出评判“刻书中心”的重要标准
由宋至明,接受官私方和各地作家学者的委托刻书,是福建建阳书坊不少刻书家的共性,也是建阳由宋及明位居全国刻书中心的主因。
笔者将此观点落实到对刻书家的功能辨析上,且以此评判福建各地一些后起的书坊,如福州南后街、连城四堡、泉州等。认为能否吸引和接受官私方,尤其是外地人士前来,并借助书坊的刻书技艺来出版他们编撰的著作,是评判地域刻书能否称为“刻书中心”的最重要标准。此举意在强调刻书中心对外的辐射和影响,目的是为了纠正在地域文化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滥称“中心”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仅是福建一地所独有,其他省份也普遍存在。因此,这一标准对全国的出版印刷史研究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力图纠正此前对某些古籍刻本刊印地点的误判
由于刻书家生平史料缺失,古籍刻本的鉴定很容易产生误判,为摒除此弊端,笔者有如下主张。一是对刻书家史料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加以详考,以此为刻本刊刻的具体年代提供依据。如徐经孙(1192—1273),宝庆二年(1226)进士。曾在福州刻印宋任渊注黄庭坚《黄山谷内集诗注》二十卷。现有的史料,均不署徐经孙官福州的具体年代。明王应山《闽大记·名宦传》载其:“宝庆间(1225—1227)官福建提点刑狱”,如以此推断,此本似刊于宝庆间。其实不然,徐既为宝庆二年进士,而宝庆前后仅有三年(1225—1227),以此论之,他一中进士就必须官居福建提刑,显然,这种可能性极小,且与史志所载其生平从中进士到官福建提刑期间有20多年历官州县的经历明显不符。此外,徐经孙《黄山谷内集诗跋》云:“刻之闽宪,始与芗城所刊《芗室外集注》并传之。”指的是淳祐十年(1250)史季温在福建路提刑司刻印其祖父史容(号芗室居士)作注、北宋诗人黄庭坚撰《山谷外集注》。则徐氏刻本,显然应在淳祐十年以后。检《南宋馆阁续录》,方知其官福州的准确时间,为景定元年(1260)。以此推知徐氏刻印宋黄庭坚《黄山谷内集》,应在景定初。
又如陈宗夔(1522—1566)刻印宋郑樵《通志二十略》,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著录清金匮山房重刊本时提到,因卷前有正德三山龚用卿序而误为明正德刊本,今人多延续此误。笔者据其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仕宦闽中,认为此书即刊于其时。且据《嘉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陈氏出生于正德二年(1507),而正德前后仅十六年(1506—1521),一个在正德间年仅10多岁的外省幼童断无在闽刻书之理。
何继高在万历二十年(1592)官福州知府时,曾重修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福州府刻本《玉髓真经》,同年又刻明周述学撰《云渊先生文选》。而其刻本,还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刊刻明王畿撰、明李贽评《龙溪王先生文录钞》,同年刊明释豁渠撰《南洵录》。本书据清李卫等撰《畿辅通志》所载,何继高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已官长芦盐运使推断,以上四种刻本分别为两地所刻,后二书的刊刻地点则不在福州。
二是主张应以具体的刊行地点为评判标准,而不宜以刻书者的籍贯为刻本的依据。
以刻书者的籍贯作为刻本的依据,是很普遍且基本没有引起学界重视、也无人去认真纠正的一种现象。本书搜录了包括福州陈孔硕、黄唐、朱端章,建宁府袁枢、宋慈、朱鉴,泉州庄夏、留元刚,莆田郑寅、蔡洸、黄汝嘉、许光裔,南剑州陈正同、廖德明,邵武叶武子、廖莹中等,由宋至清约190多位在外地刻书的闽籍人士。这些人士所刻之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误认为是闽版古籍。
不仅如此,外省也有不少同类著作,也出现了把游学或仕闽人士所刻之书,误为该省的刻本。如吴革于咸淳元年(1265)在建宁知府任上刻印朱熹《周易本义》,因其为九江人,此刻本《周易本义》被今人误为江西刻本。歙县倪士毅于至正三年(1343),在建阳委托书商刘氏日新堂刻印《四书辑释大成》,被安徽学者误认为是古徽州刻本。福建提学副使游明在闽刻《史记集解》等书多种,因游是丰城人,故其刻本被误为是江西丰城刻本。屠本畯官福建盐运司同知,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在闽考订并刻印徐火勃编《闽中荔枝通谱》,今人往往因其为鄞县人氏,将此本误为浙版。
余锓、顾霑宦闽,于嘉靖十九年(1540)在闽县刻印明胡世宁《少保胡端敏公奏议》,因二人均浙江人氏,故此本又被误为浙江刻本。实际上,此刻本刊刻地点在闽县。
这种相互混淆的现象,若不加以纠正,对福建刻书业的评价和各地刻书的认知,势必会造成一定困扰。为此,笔者特地将福建历代刻书家分为在本地刻书和在外地刻书两种类型,意在借此纠正前人的失误。
通过梳理可见,由宋至清,有不少仕宦在外的福建人士曾在江西、湖南、浙江、广东、江苏和广西等地刻书,从而使福建刻书从版本、内容、形式到版刻技艺等方面,与各地的刻书形成了交流与融合的各种可能,促进了各地刻书业的共同发展。此举既有别于此前学界普遍将闽人在外地刻书与福建本地刻书混为一谈,也在福建刻书与外地乃至全国刻书相互影响上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另外,以往的福建出版印刷史研究,由于对史料的挖掘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欠缺,遗漏了不少有价值的出版界人士。书中于此增补了刘峤、邹柄、邹栩、谢克家、徐经孙等由宋至清100多位刻书家,对福建出版印刷史做了有益的补充。
三、《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之研究方法
1. 从个体的特性中寻找群体的共性
该书以历史上一个个具体的刻书家为研究对象。其长处是可以把每一位刻书家的事迹尽可能描述得比较细致,且对前人出现的失误加以纠正;短处则是刻书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不足。为扬长避短,笔者在高度关注发掘个体特性的同时,也注意寻找刻书家群体之间的共性与内在关联。
比如,将全闽分为九地,实际上就是将全闽的刻书家分为九个群体,分析各地之间的特点,就是分析各个群体的个性是什么。如前所述,刻书中心既然在建阳,那么,建宁府建阳之外的其他八个群体与刻书中心之间有何关联?这在书中不可避免地要加以探讨。实际上,这也是隐藏在全书各卷之中的一条伏线,以此勾勒刻书中心建阳对其他八地(即八个群体)潜在的各自不同的影响。为此,作者在各卷之前均有一篇小序。内容除介绍各地刻书的概况之外,揭示与刻书中心的关联,也是其中的要点之一。
如论福州刻书,其特点是北宋中后期以寺院刻书为主,南宋、元明时期均以官府刻书和私家刻书为主,坊刻则罕见著录。“入清以后,由于建阳刻书业逐渐衰败,福州坊刻于清中叶迅速崛起。南后街、三坊七巷一带书坊,承担起了原由建阳书坊所承担的接受官私刻书的大部分重任。”以此揭示了福州刻书与建阳刻书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以及传承效应。
又如卷二的小序,认为“建阳能够连续历经宋、元、明三朝,都是全国刻书中心的主因,是它能吸引和接受各地官私方的委托刻书,这是‘中心’最主要的作用。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就不是中心”。进而提出,学界通常认为“除建阳外,福州、莆田、泉州、汀州、邵武等地的书坊业也很发达”的观点有误。“历史事实是,这一时期福建其他地区的坊刻并不发达,主要是官府、私家刻书,是在建阳坊刻的辐射和带动下,与建阳坊刻形成互补和共同繁荣的局面。入清以后,建阳坊刻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才有连城四堡、福州南后街和泉州等地的书坊。”此中揭示的是福建坊刻印刷在明清之际此消彼长的历史交替。
在卷四小序中,提出宋代莆田的刻书活动和书坊刻书业相对薄弱。与建阳相比,“莆田的‘文献名邦’之‘名’主要表现为藏书家众多,而建阳则以刻书见长。”即使是建州较晚、刻书业相对滞后、从明中后期才有刻书相关记载的福宁州,在对建州之前的福宁文化做一番考察后亦可发现,南宋时期的宁德名士与福建刻书业早已存在密切联系。如宁德林駉编纂的类书《古今源流至论》宋元时期就在建阳书坊被频频翻刻,跻身于明代建阳坊刻本畅销书之列。以上所论,厘清了刻书中心与其他八个群体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关联。
此外,由宋及明,接受各地作家学者、官私方的委托刻书,是福建书坊许多刻书家的共性。如晁谦之绍兴七年(1137)官福建路转运判官,编辑并刻印其从兄晁补之撰《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刊刻地点是在刻书中心建阳。绍兴三十二年(1162),龙舒居士王日休著《龙舒净土文》,也是在建阳书坊刊印的,为王日休此书初刊本。据卷末《参政周大资跋》所云:“又将亲往建安,刊版于鬻书肆中,汲汲然若不可一日缓者。”此言建安书肆,即建阳书坊。明代,则有建宁知府杨一鹗,嘉靖三十九年(1560)受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吉澄之托,在建阳刻印《春秋四传》;嘉靖四十二年(1563),受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李邦珍的委托,在建阳刻印明朱衡撰《道南源委录》。
2. 将史料的辨析与版本的辨误,尽可能地贯穿到全书之中
由于刻书家生平史料稀缺,使古籍刻本的鉴定容易产生失误。为此,笔者将古籍刻本的刻印地点、年代与刻书家的生平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纠正了以往的不少疏漏或讹误。
如永嘉郑伯熊于乾道五年(1169)任福建路常平司提举。时常平司设司建宁,其于此整理《二程遗书》《二程文集》《经说》诸书,作小字本刻印于建宁府。其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为一集,建宁所刻本。”此处对“建宁所刻本”的编者、刊刻者均未作明示。本书通过运用朱熹、周必大存世的两通书信的考证,得出陈振孙所言“建宁所刻本”,实即郑伯熊建宁常平司刻本。
又如,在“汪应辰”条中,对邹道乡、邹德久父子字号两个错字的辨析;对刻书家两位刘震孙、两位胡琏、两位冯孜、两位李春熙、两位朱霞、两位林同的辨析;以及两位号“磊老”的学者吴雨、傅汝舟的辨析与纠正;对刻印《读史管见》的孙德舆,是否是胡大壮之子的辨析,通过分别从刊刻时间、地点,乃至刻本的归属等若干方面的考证,对史籍或当代研究成果中所出现的失误予以一一纠正。
3. 通过史料的辨析,追溯刻本版权的归属
一般来说,刻书牌记往往是鉴别古籍刻本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历史的复杂性,表象往往会掩盖真相。如建阳书坊有不少接受官私方委托刻印之书,往往也会出现书坊的刻书牌记,从而造成对刻本版权的误判。书中列举了明正德间建阳书坊刘洪慎独斋刻本《文献通考》《群书考索》等,目录后虽然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独书斋刊行”等牌记,但从这些书系福建按察司、建宁府、建阳县等出资方来说,刘氏慎独斋只是接受委托刻书而已,故其版刻性质应属官刻。
这一现象,还往往下延至清代福州的许多书坊。如清嘉庆年间,福鼎王遐春麟后山房辑录并刊刻《王氏汇刻唐人集》七种,委托闽县吴大擀刊印。清光绪年间,榕城王友士为刘尚文刊刻《莆阳金石初编》,有“光绪庚子刊于福州”长方牌记,右下角有“王友士锓板”五字。同治十三年(1874),王凯泰委托吴玉田在福州刊刻《归田唱和集》《湖上弦歌集》等,牌记题“俭明简斋雕版福州”,卷末有“三山吴玉田镌字”。以上数例,均为私家委托书坊刊印图书。
为保证史料辨析与版本辨误的正确性,就必须在史料运用方面下功夫。为拓展学术视野,笔者尽可能地扩大对史料的搜集范围。在史料运用方面,除大量阅读宋明以来的正史、方志、笔记和文集,关注学者通常习用的文献之外,还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刻书家的族谱、家乘、碑铭等材料,乃至在出版史研究领域中通常不为所用的摩崖石刻等。通过运用新的史料,为纠正以往错失提供更多文献佐证。
如宋淳熙十年(1183)司马伋历官泉州知府,重刊《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泉州清源山莲华峰有司马伋视察水利题刻云:“淳熙十年,岁在昭阳单于涂月立春日,陕郡司马伋相视水利竟事,因登此峰。”由此可知,司马伋任泉州“郡守”的准确时间,正与刊刻此集的时间吻合。
明樊献科,则分别在福州乌石山天北、武夷山水帘洞崖壁有两条石刻,这些石刻,对判定樊氏刊刻《性理大全书》的具体年代均提供了有益的佐证。
清光绪延平知府张国正,曾刻印宋罗从彦《罗豫章先生集》、宋杨时《宋儒杨文靖公全集》。民国《南平县志·学校志》对其生平仅有两条非常简略的记载。为弥补此不足,笔者考辨张国正在武夷山天游峰顶胡麻涧岩壁和福州鼓山龙头泉所镌的两方摩崖石刻,充实了其在闽仕迹。
四、《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之不足
部分刻书家的生平事迹,史志罕见记载。一些在刻书史上声名卓著刻书家,如南宋余仁仲万卷堂、蔡梦弼家塾、黄善夫家塾、建安蔡琪家塾、刘叔刚一经堂、魏仲举家塾、元建安虞氏等人的事迹,除了在他们刊刻存留后世的若干种刻本中,偶有一些有关堂名字号等零星信息之外,其他生平事迹均已无从查考。他们相关的刻书活动和刻本概况,在笔者的《建阳刻书史》以及学界同道的同类著作中,多有述及,因无更多新的史料,故在书中从略。基于同样原因,原先搜集的还有70多位虽有刻书事迹,但其生平事迹无从详考者,最终成书时也只能舍弃,可谓该书一大遗憾。史籍浩瀚,误读误判,在所难免,若有谬误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本文原载于《印刷文化》;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