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成了百姓休闲的地方
——战国时代的纵横家苏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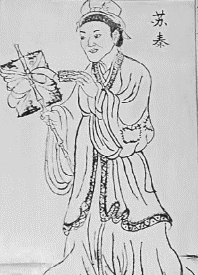
战国时代有一种人,博闻广见,能言善辩,经常游说于诸侯国之间,被称为纵横家。《汉书?艺文志》指出,“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使者)之官”,“受命而不受辞”,并将之列为“九流”之一。至于“纵横”名称的由来,则是因他们当中有两大对立派别——“合纵”与“连横”。其实,按现代的话说,所谓纵横家,乃从事外交活动的谋士。苏秦就是著名的一个。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年轻时曾求学于鬼谷子(此人擅长纵横捭阖之术,据说孙膑、庞涓均是他的学生)。之后多次出游,但都没有得到赏识。回到家里,父母不跟他说话,嫂嫂不给他做饭,连一贯对他敬重的妻子也只管织布,不肯下机。众人还耻笑他,说人家都是靠“治产业”或从事工商业致富,你倒好,凭一张嘴就想出人头地,难怪穷困潦倒。苏秦听后甚感惭愧,从此更加发奋读书。据《战国策》记载,他读书每天至深夜,有时困了,精神不够集中,就用银针刺痛大腿(即“锥刺股”),使人清醒过来。苦读一年之后,苏秦自我揣摩,认为“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便先后去游说周显王和秦惠王。周显王的左右对苏秦非常了解,觉得他说的都是老一套,没啥意思,根本不愿听;秦惠王则刚刚把变法的商鞅杀掉,对能言善辩的人很讨厌,自然不用。苏秦随后到了赵国,当时赵国的宰相是赵肃侯的弟弟,号奉阳君,对苏秦“弗悦之”,即不喜欢。让人不喜欢,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虽然一再碰壁,但对自己的主张充满信心的苏秦并没有气馁,他继续游说。先是来到燕国,他对燕文侯说,燕国是个富庶之地,“所谓天府者也”,但毕竟国家小,力量有限,经不起外部侵略。燕文侯点头称是。苏秦接着说,然而这些年来,燕国却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大王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侯请他解释。他说,原因在于“赵之为蔽其南矣”。即赵国在前面挡住秦国,使秦不敢轻易对燕国用兵。又说,赵国作为屏障,与燕国紧靠在一起,如果想攻打燕国,早上发兵晚上就到了。可见对于燕国,赵国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希望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燕文侯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高兴地对苏秦说,“子必欲以合纵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意思是,你想用合纵的办法保证燕国的安全,我把国家都托付给你了。
苏秦随后到了赵国。当时奉阳君已经去世,没有了“拦路”的人,苏秦得以见到赵肃侯。他先是指出,“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不安”,接着纵论天下形势,认为秦在诸侯国中最为强大,它一心要吞并六国,却又一时下不了手,原因是有顾虑。如秦之所以不敢举兵伐赵,在于背后的韩、魏。但这种情况并不能永远维持下去,有一天“韩、魏不能支秦,必人臣于秦”。谈到这时,他提高嗓门说,六国的土地加起来,超过秦国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如果能联合起来抗秦,秦国必败。最后他作了总结,“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也就是说,联合抗秦可以彻底改变目前的形势,对六国有利。
赵肃侯听了苏秦的分析,深表赞同,“寡人年少,立国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今上客有一存田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并立即拜苏秦为相国,还赏赐给他一百辆车马,一千斤黄金,一百双玉环,以及许多丝绸锦绣,让他去游说其他国家,以期实现六国联合,订立合纵盟约。苏秦接受这一任务,先后去了韩、魏、齐、楚等国,与它们的最高统治者谈论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并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分别将他们说服。公元前318年,齐、楚、燕、赵、魏、韩等六国的国君,来到赵国的洹水开会,正式签订合纵盟约。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矛头直指秦国。会上,苏秦被六国一致推举为“纵约长”,挂六国相印。“纵约长”这一职务,不似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倒有点像“北约”或过去“华沙条约”的秘书长。而这个时候的苏秦,个人事业达到了顶峰。
风光无限的苏秦衣锦还乡,一路上前呼后拥,受到各诸侯国的礼遇,接待规格几乎与帝王一样。路过洛阳时,周天子专门派人清扫街道,让大臣到郊外迎接。回到家里,苏秦的弟弟、妻子、嫂嫂都不敢正面看他。苏秦问嫂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嫂直言回答,因为你现在“位尊而多金!”苏秦听后感慨万端,“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从这番话可以听出,苏秦对地位和富贵荣华是看得很重的。
由于合纵联盟发挥了作用,秦国对它东面的六国不敢轻举妄动。据《史记》载,“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但是,秦惠王并非无能之辈,他知道,要改变目前的形势,必须破坏合纵联盟,于是采纳张仪(与苏秦同学)的“连横”策略,离间六国之间的关系。他先是将女儿嫁给燕王的儿子,之后又退给魏国几座城池,燕、魏两国国君看到秦国的这种友善态度,都和秦国好了起来。
赵肃侯得知燕、魏与秦国修好的消息后,甚感不安,便把苏秦找来,责问他说,你倡导合纵联盟,又是六国的纵约长,可盟约签订还不到一年,魏国和燕国就让秦国拉过去了,你看今后还怎么办?苏秦忙说,大王您别急,让我去燕、魏两国走一趟,定可将事情办妥。
苏秦到了燕国,当时燕文侯已经死了,太子继位,是为燕易王。看到苏秦的到来,燕易王气冲冲地对他说,当初先君听了您的话,支持合纵抗秦。按说六国之间,应团结一致互相帮助才对,齐国却趁先君去世、办丧事期间,无端抢走了我们的十座城池。对于这样的侵略行为,你作为纵约长,总应该主持公道吧?苏秦此行原本是来纠正燕国亲秦倾向的,没想到燕易王先行告状,使他不得不掉头去齐国,为燕国讨回失去的城池。
在赴齐国途中,苏秦深思熟虑,早已成竹在胸。一见到齐宣王,他先行祝贺礼,接着又行哀悼礼。齐宣王被这些动作弄得一头雾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问道:“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苏秦回答说,我到大王这里来,自然应先行祝贺礼,可是看到齐国和您将有大难临头,便只得再行哀悼礼。齐宣王急问,齐国和我会有什么大难?苏秦说,当今燕王是秦王的女婿,您把燕国的十座城池夺走,不就得罪了秦国吗?如果燕国借强秦的力量与齐对抗,后果不堪设想,这不是大难是什么?齐宣王说,哪可怎么办?苏秦说,“臣闻古之善制事者,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说到这里,他稍作停顿,然后指出问题的实质,意思是,倘能归还十城,“则大王号令天下,莫敢不听。是王以虚辞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听了苏秦的这番话,齐宣王心里非常爽快,当即答应“乃归燕之十城。”
苏秦回到燕国,因为有人诋毁,说他是“左右卖国反覆之臣”,燕易王因此没有让他官复原职。苏秦感到委屈,便向燕王申诉。他说,臣的老母亲住东周洛阳,我没有在她老人跟前尽人子之孝,而是风尘仆仆地为大王的事业奔走,却受到如此对待,您说公平吗?燕易王听了,觉得苏秦的确被误解了,立即为他“复就故官”,并“益厚遇之”。但由于种种原因,苏秦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燕国,到了齐国。齐宣王收留他,拜他为客卿。
此时的六国,合纵联盟已经瓦解,苏秦也没有了往日的声望。虽然后来的齐湣王仍旧善待他,但他在齐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许多大夫与他争宠,甚至收买刺客想暗杀他。有一天,苏秦终于被人刺中要害,齐湣王派人追捕刺客,却怎么也抓不到。苏秦虽已生命垂危,但神智仍然清楚,他向齐湣王建议,“臣即死,车裂臣徇于市,说‘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苏秦一生都在用计,最后这一计,以自己被戮作为代价,更是出人意料。齐湣王听后当即下令贴出悬赏告示。刺杀苏秦的人,以为自己有赏可领,便主动露面,结果上当,终于被抓住。
读苏秦一生,深感此人才华横溢,足智多谋。然而他的命运却又是那样的多舛。首先是为之奋斗的合纵联盟,由于受到老同学张仪采取“连横”策略予以针对性的破坏,更由于联盟各国的领导人目光短浅,互相猜疑争斗,结果被强秦各个击破,终于土崩瓦解。自己也因此成为悲剧性人物。其次是最终的“车裂”(即所谓五马分尸)。尽管已经临近死亡,尽管目的是为了抓到凶手而不得已出的计谋,但如此“下场”还是让人叹息。《史记》作者司马迁对苏秦似乎抱有好感,才会用一个完整的篇幅详尽记载传主的一生(与他作对的张仪就没有这个“福分”),并在篇末写道:“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领恶声焉。”


